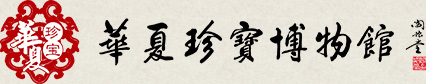- 【新闻中心】
- 马凯臻:李砚祖让陶瓷艺术自说自话 2013-12-03 02:10:43
马凯臻
艺术学 学者
李砚祖教授一开始就带着对陶瓷艺术本体意识的文化自觉,进入他的瓷绘创作。仅此,就使砚祖先生的瓷绘作品,有了一种挺进陶瓷艺术内核的文化势能,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对于所有从事陶瓷艺术的艺术家来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那道坎儿,当然有造型的功夫、有审美的眼光、有技术的能力等,但顶要紧的还是对陶瓷作为一个生命体的透彻领悟。后者如果缺失,他或许是一个挺不错的国画家、油画家、雕塑家等,但他绝对称不上是一个优秀的陶瓷艺术家。
李砚祖先生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艺术设计史论、美术史论及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他还是江西省政府特聘的“井冈学者”,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特聘教授。在李砚祖的讲学目录中,《中国陶瓷艺术》是重要的一门课程。以上这种世俗的职务罗列当然不是为了身份的炫耀,而是由此可见,相对于众多陶瓷艺术家,李砚祖迅速且无障碍地进入了陶瓷艺术内核的逻辑纵贯线。
但是,作为艺术理论家,特别是对陶瓷艺术有专门研究的理论家,对陶瓷艺术本体有基本的了解并不是困难的事。对任何人来说,只要有一份与陶瓷艺术长期厮守的实践阅历,甚至无须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可要强调的是,这仅是迈进了对陶瓷艺术认知的第一道坎。我坚持认为,对陶瓷艺术的理解与认知有三个层面。其一,是“物性”认知,即第一个层面,这是对理解陶瓷艺术的基础层面。无须赘言,它几乎是所有真正的陶瓷艺术家的共识,也是陶瓷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必须遵循的。“物性”的差异是陶瓷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根本区别,也是许多绘画基本功、艺术领悟力虽强于专业瓷绘者的架上艺术家,却在进入陶瓷艺术创作后,由于缺乏对“物性”的自觉意识,而左右都觉尴尬的关键所在。因为,在他们那里,材料转换了,处理架上语言的思维却没有转换,他们面对的是陶瓷材料,却一味向水墨或其他绘画形式低眉顺眼,以致产生出的所谓陶瓷艺术作品,不过是尚未跨入陶瓷艺术基础门槛的一次带有“反串”性质的娱乐而已。但是,了解“物性”,不等于尊重“物性”。比如,就有瓷绘作者利用对陶瓷“物性”的知根知底,成功完成了对油画效果惟妙惟肖的模仿。应该说,这仅是对陶瓷“物性”的利用,却不是对陶瓷“物性”的尊重。这种离开陶瓷生命本体,强迫它靠近其他艺术形式的种种努力,其实是对陶瓷的非分要求。这是技术的成功,却不是陶瓷艺术的胜利。更进一步说,所有的这些技术上的努力,都是对陶瓷艺术的阉割,并令其失语。这种缺乏纯粹的陶瓷本体语言的陶瓷作品,连同上述的“反串”表演,我称之为“泛陶瓷艺术”。
“泛陶瓷艺术”与消费文化的泛滥不无关系,它构成了现下陶瓷艺术不可逃避的文化语境。那么,以此为背景,我们去看李砚祖教授的一系列作品,包括高温颜色釉、釉里红、窑变、青花、斗彩等,自然会品咂出令人反省的、并与当下铺天盖地的“泛陶瓷艺术”拉开距离的文化意味。这种距离,标志着艺术家对陶瓷艺术的认知,这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即从对陶瓷艺术的“物性”的理解,跨越到对其“物自性”的尊重。简单说,就是让陶瓷艺术自说自话,让陶瓷在自己的躯体里安妥自己的灵魂。萨特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观察一粒石子,而在于如何进入它的内部,以它的眼光去看世界。”我的理解,“观察一粒石子”是追求“物性”的认知,而“进入它的内部,以它的眼光去看世界”才是摆脱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一厢情愿。我觉得,砚祖先生对陶瓷艺术的追求,正是以对陶瓷“物自性”的尊重为依托的。李砚祖近期创作的一批华美丰赡的窑变瓷绘山水,如《江岸飞红千山秀》、《江山多娇》等,就是极好的例证。对此,我们不妨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与之比对与辨析,以便求证陶瓷艺术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以及李砚祖通过瓷绘创作对这种存在方式的深度认同。表面看,李砚祖的这些窑变山水虽然与张大千的泼墨山水有某些相通之处,却不可以与之作简单的类比。否则,其意义空间便被圈定在一个利用对陶瓷“物性”的熟练掌握,以“窑变釉色”模仿“泼墨”效果,从而完成一种艺术“反串”的低级层面上了。因此,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在张大千那里,宣纸的“物性”特点被充分利用,所呈现的,是带有强烈的艺术家主观情绪的泼墨(包括泼彩);在李砚祖那里,陶瓷的“物性”特点不是被利用,而是被开发。换句话说,张扬情绪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陶瓷本体。李砚祖要做的,只是通过自己对陶瓷“物性”(也包括对釉色的料性)的潜心研究,帮助陶瓷建立起专属自己的“语感”世界——窑变。泼墨,是张大千作为“人”的艺术标签;窑变,则是陶瓷作为“物”的文化符码。所以,两者的文化认知意义有着根本的不同。砚祖先生心中明了,陶瓷艺术的生命母体来于自然,它比任何艺术形式都渴望保持,并向人类暗示这种非人力而为的自然存在。事实上也是,我们去看这批窑变作品,那种或漂浮或沉稳的幻觉感,那种丝丝缕缕、重重叠叠的微妙的肌理变化,是艺术家无论怎样血脉贲张地或泼或洒都无法完成的。由此可见,对陶瓷“物自性”的自觉寻找与发现,构成了李砚祖的智慧与精华。李砚祖正是通过对陶瓷自身语言能力的信任,并忠实于它,最终展现了这组窑变山水的文化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看到了李砚祖教授扎实的绘画功底,却在这篇文字中着意回避的原因。我不想将他的陶瓷艺术作品带入绘画,特别是中国画的评价体系中,因为,那不是陶瓷艺术的本体美学特征,它有可能会诱使人们只在陶瓷艺术的表层意义上打转,而忽略了李砚祖教授对陶瓷艺术最有价值的贡献。
当然,一部瓷绘艺术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将笔墨带入瓷绘的历史,而且,釉上的古彩、粉彩、珐琅彩正是由此产生并佳作频出的历史。所以,李砚祖教授既然将陶瓷艺术划入自己的学术领地,那就不可能漠视这一存在。因此,在砚祖先生的作品系列中,釉上彩的研究自然占有了一席之地。最近,砚祖先生连续推出的釉上粉彩山水、花鸟即为这一研究的成果。但是,应该指出,虽然形式上砚祖先生不弃传统,但在视觉呈现上,他却将现代的审美元素带入了创作。这里有对山石阴阳向背的强调,有对空间层次的开掘,也有对体积与色彩构成关系的讲究,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与加强了传统釉上彩的表现力,从而也推动了这一传统的手法的现代呈现。如果再结合砚祖先生的高温窑变作品来看其与之迥然不同的釉上彩作品,就会发现,砚祖先生的创新与开掘,不是一时的灵感所致,这中间必有一条生命体征相似的脐带。显然,脐带的一端是对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表达,另一端则是当代的审美感知。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在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学术审视与深度理解的过程中发生的。使砚祖先生占据当代瓷绘艺术制高点的是,李砚祖教授在这两端之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来往自由,羁旅有痕并使之相互砥砺,联动发展。而这正是活跃在景德镇的瓷绘艺术家们深深短缺的。
砚祖先生瓷绘艺术中对“物自性”的尊重,还体现为对“器”的尊重。当下,许多标榜为陶瓷艺术的作品,却是“画”与“器”隔着一层皮,它们看起来也漂亮,但在材料上,不过是从平面到“器”的简单挪移;在表现力上,不过是寡味的心灵鸡汤,没有陶瓷文化的浓厚意味,因而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应该说,这类作品,仍然属于“泛陶瓷艺术”的范畴。与之不同,李砚祖的创作,由于对陶瓷艺术的本体美学特质的深刻把握,总能让我觉察,“器”在李砚祖的眼中,绝非一个或圆或方的视觉形态,“器”实则是一个与所在空间,与创作主体,以及与接受对象发生不同关系的生命存在。这一点,也显示出李砚祖不同于一般瓷绘制作者,尽管器形千般变化,可还是被当做一幅画去处理的认知差距。所以,李砚祖教授一系列的瓷绘作品,无论是釉里红、青花、高温颜色釉,还是窑变,都能因为贴合并融入不同器形的表达语感,并最终实现“画”与“器”的异质同构,如同毛细血管与肌体,两者妙合无痕。这些作品,或可以随形而动,徐徐展开,使物象在空间的转换与时间的流动中渐次呈现,收卷自如,毫无断裂感,如《荷塘翠鸟》;或可以使物象随“器”的结构水一样自由流转,灵魂附体般有序蔓延,向不同的体面从容过渡,从而凸显与强化“器”的体积感与空间感,如《荷塘清香》;或可以在极简的器形结构中,让承载艺术家心路的线条或散漫或有序地缠绕攀缘,使“形”的单纯与“线”的丰富对立统一,相交融汇,气韵弥漫;或可以利用镶器的垂直面,压低视平线,以此强调平面的视觉高度感,并为近、中、远景依次推至高耸于天际的峰巅,提供空间可能,同时配合器形的横面展开,形成无焦透视的全景视域,如《江山高秋》等。我们看到,李砚祖的这些努力,都会带动接受对象摆脱对“器”的功用性,以及“画”的装饰性的浅显认知,而被引向更有趣的视觉审美体验与更深远的美学思考。
当然,对“物自性”的尊重,并不是要放弃“人”的作用。反而,我们要强调的正是“物”与“人”的结合与互动。这便是我所说的对陶瓷艺术认知的第三个层面。陶瓷艺术尊重“物自性”,而作为艺术的一般规律,却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这并不是一种认知悖论,而是陶瓷的特质决定了它的艺术表达必须有一个规定,就像格律规定了格律诗、足尖规定了芭蕾舞。陶瓷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在这种严苛的规定下,将“物”的自然与“人”的自然,同构到一个生命体中。而这应该就是陶瓷艺术的至高境界。就像李砚祖的瓷绘作品,可以将釉里红的天工之美与艺术家注入的主观气息熔铸一体,如青花釉里红瓷瓶《红树林》;可以借高温颜色釉的色彩层次与光影迷离,帮助艺术家突破想象力,使普通自然界的物象与情感得到意料之外的呈现,如《多子图》;可以将不可控的釉色流变与可控的造型结构结合起来,并藉此形态且诗意地叙说着自己,等等。这里,特别应该说到的是,从砚祖先生的一批高温窑变作品,如《春山高隐》、《江山多娇》、《匡庐圣境图》等作品中,更可以看出人与物、艺术与技术等多维度的纠葛、碰撞与相互迁就,相互礼让。我们知道,在瓷绘作者那里,瓷绘艺术的生命本体,一般都是被水墨山水的各类皴法及线条所掌控,从而令自身委屈地去适应宣纸的“物性”特点。因此,它便很难超出被水墨山水的评价标准所规定的阅读视域。而李砚祖的这批窑变山水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它不再向水墨的规定性献媚,它以自己的语言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窑变山水从创作伊始,即在陶坯的绘制阶段,就与水墨的表现方式分道扬镳,这一阶段中,艺术家的着力方向不是勾勒皴擦,让山水视像即刻呈现或半呈现,而是依赖对釉料“料性”的充分了解,让含有不同矿物质的色块相互叠加。同时,想象在炉火的催动下,不同釉料相互影响后的不同表现。它的艺术与技术的趣味在于作品的最终效果是不可控的,但这并不等于艺术家面对釉料“料性”的放任而束手无策。通过砚祖先生的这些新作,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窑变的范围与形态,它所呈现的点与面,如他的窑变山水系列作品,那山顶的红、裸岩的黄、远山的蓝与视觉主体大面积翠绿,构成的富有强弱节奏的对比与呼应;窑变色彩由表及里的幽深的层次构成,如《春山高隐》丰富中此隐彼显的翠色等,还是要通过艺术家自身的艺术感悟、技术能力对陶瓷本体施加才可以完成的。上述作品都让我们看到,李砚祖充分调动了自己的好奇心,不断地去叩问:陶瓷作为一个生命体它究竟需要什么?一方面,李砚祖先生以实证的态度、技术的分析对陶瓷的本体特质进行描述,他要让陶瓷的生命本体对火,对釉,以及对“人”施加过来的真实感受传达出来;另一方面,李砚祖又将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使之成为陶瓷艺术表达的一部分。
显然,李砚祖教授以他对陶瓷艺术深刻的理论沉思,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以及在两者之间的来往自由,相互催动,在当下“泛陶瓷艺术”泛滥的文化境遇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也为陶瓷艺术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参照物。它提示我们,如果说一般的艺术样式强调的是对个人气质、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的把握。那么,对陶瓷艺术来说,还要将“材料性格”这一关键的要素列入其中。而且,只有在对“材料性格”服从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其他三者的追求。缺失了这一点,就等于抽去了陶瓷艺术的生命。
最后,我特别想说,李砚祖先生的陶瓷艺术创作,不是出自简单的艺术追求、自娱自乐或利益索取。他不会在潜心创作中迷失自己作为学者的角色身份。他一定有着强烈的角色意识,并由此生成一种责任意识。特别是,作为江西省政府特聘的“井冈学者”,作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特聘教授,李砚祖一定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现状深怀忧患意识。李砚祖这些年,频频来往于瓷都景德镇与国内其他各地、乃至国外,景德镇在中国历史“文化地形图”上的鼎鼎大名,与当下的文化贫瘠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一定令他纠结在中国陶瓷何去何从的文化乡愁中。我更以为,李砚祖教授一定与纯然端坐书斋的理论家不同,也与纯然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不同,他一定是将这种文化乡愁凝集成理论的能量与创作的冲动,以身份推动创作,以创作申明身份,并形成不断前行的动力机制。因此,作为有艺亦有道的李砚祖陶瓷艺术的发展前景,便更值得人们去期待。
版权所有:北京华夏珍宝博物馆 京ICP备12006144号